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rresponding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30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in 2017. It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spatial explor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fus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has typical north-south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whil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how the pattern trend of decreasing from coastal area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two is between 0.446 and 1.000, with a certain level of coupling, an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is between 0.288 and 0.619, and the overall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The global Moran'I index value is 0.185,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dependence, and the local self-correlation results show no "low-high" and "high-low" regions, and most area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significant spatial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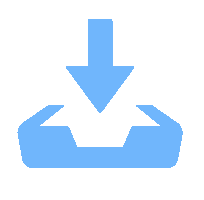 下载:
下载: